本文转载自知乎@钟子默 先生的《宅社会学与坑》专栏,是研究GalGame(此处特指《素晴日》)与社会关系学的重要文献。原文分上、中、下三部分,本文为第一部分。本文的所有知识产权均归属@钟子默 先生所有,再次向@钟子默 先生表示感谢。
性别视角下的素晴日(上)
(注:本文涉及游戏序章、第2章、第3章的严重剧透,请读者谨慎阅读)
系列前言
二次元中的性别话题并不少见,尤其是随着二次元消费文化的繁荣昌盛,具备符号价值并承担着象征交换功用的性别符号也逃不开商品狂欢。我们可以随口举一个耳熟能详的例子:“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子”。这句话放到如今的互联网中未免有一点过时,但它曾与“小姐姐”一词一度构成了宅文化的盛景,而且引发了非宅人士的圈层效应。另一个非常常见的例子是,我们(不论男女)对女性角色,尤其是女性身体(胸、腿)、女性气质(一些萌点)的执着,在二次元享乐中体现得玲离尽致。由是观之,性别已是讨论二次元文化逃不开的话题。
对女性气质的消费并不完全是一种父权制异化的产物。面对具体的作品,我们暂且放下意识形态的担子,以阅读经验为依据从性别社会学视角介入问题。换言之,性别是解释社会与个体的诸多变量之一,以性别为主要变量研究,不单单要考虑经济与政治,同样要考虑种族和个体认同的身份;性的政治性也不单单只考虑男性的“得势”与女性的“去势”的情境,还要考虑多元影响下,男女权力倒序和性少数群体的边缘化问题;在女性受到压迫的父权现实下,女性行使“拒绝”的主体性也值得关注;最后,我们的出发点是“性别视角”而不是“女性视角”也在于后现代视域下,分割男性与女性概念的薄纱被扯破了。激进意义上男女不再变得泾渭分明,更没有所谓固定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那么我们不妨看看落实到作品中,这层关系是怎么表现出来,我们又如何沉浸在审美的矛盾之处的。
作品简介
本文“主角”是圈内人基本家喻户晓的美少女游戏(gal)。汉化中文名叫美好的每一天,圈内一般称素晴日。这部作品在其发售之日其就受到了很大的关注,荣誉拿得一举拿下了萌えゲーアワード2010年度铜赏和剧本组金赏,批评空间90点台,bangumi游戏排行榜上只有十余部作品能和它叫板,位列G吧12神器之首。关于这部作品的详细信息,读者可自行搜索。这部作品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佳绩,与其剧情的哲学与文学深度不无联系,如果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这条主轴,爱丽丝梦游仙境、西哈诺等文学、新古典主义这些锦上添花的素材移除出去。整部作品也将黯然失色。确实如此,维特根斯坦早期关于世界与言语关系的看法不但晦涩艰深,诠释也存在多义性,顶着神秘主义的光环令人神往。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哲学和当代社会学举足轻重的“语言学转向”。以至于,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观分析角色和剧情成为了评论素晴日的主旋律。
然而在这里,笔者试图挖掘作品的剩余范畴,将焦点再次放到人物与剧情的关系上。尽管同样是从“人物论”出发解读剧情和世界观,绝大多数评论家面对作品中角色的性别却表现出了“迟钝”。而在笔者看来,除了哲学之外,素晴日中最值得解读的要素恰恰是人物呈现的性别与性别气质。如果将剧情中的各种异装癖、扶她、伪娘、校园性暴力要素全部归结于扶她自的鬼畜癖好,这对分析这部作品恐怕有失公允,尤其是剧情表现出的反抗与救赎的主旋律(不计“终之空”结局的话)与角色性别主体性的实践有着惊人的吻合。后面主要是从“人物论”出发,分别讨论剧中关键人物的性别气质,以及他们进行的主体实践。
鉴于性别问题的复杂性,本文将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以“女性无意识主体→欲望主体(性别展演性)→社会个体(性别社会学)”为轴,刍议原作中的性别问题。
一、想象与女性叙事
对于女性想象界的讨论不可回避拉康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和“三界”的论述。当然还有其后继者对拉康理论的“扬弃”。这些议题可以在游戏第三章窥见一二。玩家经历了第二章中二教主的洗礼后,第三章视角转移高岛柘榴身上。整篇中,柘榴的前后转变和毁灭结局令人唏嘘,但从某种角度来说,其主体性正是因为最终的妄想和癔症爆发而跃然纸上,从而占据了超越其他角色,尤其是取消了男性角色的本体论位置。从时间序列来看,柘榴也是推动整个剧情的首要因素。
本章开头叙事平淡无奇。主人公柘榴是一名文静的文学少女,天真、爱幻想、曲高和寡,不善言辞,做事有时笨手笨脚,暗恋着本作另一主人公“间宫卓司”。正如很多作品的主人公的设定一样。然而在这部充满阴谋较计的作品中,柘榴的率直和单纯为她带来灭顶之灾。章节开始就交待了柘榴遭受校园霸陵的环境,原因无外乎是不会察言观色以及和曾遭到欺负的橘希实香建立了联系。随着故事进展,柘榴和希实香的关系也若即若离,到了关键选项处,是否选择考虑自己和希实香的关系成为了章节主线和支线的转折点。
如果选择考虑希实香的事,后文会因为帮助希实香和与她建立更深刻的感情联系,餐厅事件柘榴就会揭竿而起和希实香组成战线;如果选择“先进入教室”,结果柘榴会代替希实香受到惠的欺凌,以致在餐厅事件时彻底处于被动。不幸的是,游戏主线恰恰是柘榴没有考虑和希实香重修旧好。所以在后续剧情里,柘榴被学校的男男女女折磨得死去活来,涂鸦、剪衣服、强迫全裸表演,各种剥削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第一人称的讲述更是把这种温婉到残忍的叙事转变体现的淋漓尽致。在剧情高潮处,柘榴被人灌药轮奸,直接将柘榴推向了精神崩溃的深渊里。
可以说,第三章主线到此为止值得讨论的经验分析就在这戛然而止了。取而代之的是心理分析的介入。玩家能直观地看到,精神高度污染状态下柘榴眼中扭曲的现实,贞操作为象征秩序的大他者直接具象化为神明,在柘榴的现象世界出现,并不断对柘榴的精神施压。非常细腻地描绘了遭受性侵的女性,心理的恐惧与挣扎。
剧情后半段出现了值得玩味的地方:柘榴在某中二网站上找到了两名同样遭受不幸的志愿者。其中叫宇佐美的女生神神叨叨地说她们三人都是异界女神的转世,一直在和彼岸的“物理特化符虫”对抗,还编译了一整套女神对抗魔界的中二剧情。但此时精神崩溃的柘榴竟竟完全接受了这种天方夜谭,受到极大的启发进而合理化了自己的全部妄想,进一步完善了整个妄想世界观。到章节的最后,柘榴将自己的妄想世界全盘拖出,在极其严重的精神紊乱和歇斯底里之下,拉着其他两位志愿者从高楼跳了下去,“回到了乳白色的星球。”第三章在这压抑的场面中走向结局。
正如上文提到,本章唯一的,也是最关键的选项其实涉及到了剧情形式的重要转变:选项之后,若是走主线剧情。玩家接触到的不再是柘榴和希实香两名女性角色的“关系”而是柘榴的“独白”。此时故事的重点已经从校园欺凌的社会行动问题转移到了妄想症状上。惠、聪子等施暴者、希实香、间宫卓司已从舞台上退场,整个故事的主体只有高岛柘榴一人,世界仿佛围绕她而运转。章节后半部分,所有剧情几乎都是以柘榴的世界展开。在柘榴妄想统治之下,甚至异世界设定的创造者宇佐美都感到恐惧。高岛以她旺盛的想象力和受到非人虐待的经验,创造了想象世界的中心。将异世界始作俑者的话语解释权完全褫夺。事已至此,对柘榴的怜香惜玉显得不知天高地厚,她的癫狂拒绝玩家报以凝视者的移情,反之令玩家对她产生恐惧的反移情。癫狂者形象与“被凌辱女性”形象产生了割裂。向我们展现了非实质却极具震撼力的破坏。
在卓司和柘榴疯癫状态的表现差异上,我们可以清楚发现柘榴的妄想的特点。根据伊利加雷在她第一部著作《精神错乱症的语言》里的发现,男性患者即便在发疯状态下亦保留了句法修正和使用“元语言”的能力,而女性常常经由“身体”表现她们的症状(歇斯底里)1。卓司的症状联系于被灌以救世主期待的早期经验,囤积了大量关于神秘学与邪教的知识,被欺负只是一个持续性的诱因而不具有单一的决定作用。卓司的精神病症仅仅持续了不到半个章节,便重新接受了“教主”这一锚定,重新建立了稳定的总体性观念(邪教信仰),呼唤神权。所以卓司后期传教时,冷静且严谨地阐述自己的保守弥赛亚思想。然而柘榴的妄想的症结在于“被男性侵犯”的事实,而且这一事实直到最后跳楼自杀前都未能得到承认而是被异世界妄想所替代。在柘榴无意识中,“贞洁”一直占据着一个崇高的大他者位置,“被男性侵犯”的事实根本无法接受。而宇佐美提供的不完备的世界观,却激发了柘榴的“遁入”。因为这套世界观创建了“前世”这一重要的模型和窗口,而女神则又联系于贞洁的形象。关键之处还在于,柘榴从没有将她的幻想梳理成逻辑连贯的论述,而是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疯癫状态”,最后表现为强大的肢体激动拉人跳楼。这是她和卓司发疯最大的不同之处。
依利加雷在论述女性想象界的时候,提到女性想象界具有多样性、易变性与流动性特点。相对的,男性则是同一的、合理性的。同样是寄托于“自恋”,卓司的认同联系于现实秩序的妄想重构,意指了从被剥夺者转为剥夺者的欲望与承认。而柘榴的认同则呈现出癫狂的不确定性,试图完全逃离象征秩序的约束。最终赋予了认同的神话色彩,这种象征界的逃离并不发生在自己被强奸之后,而是早在故事呈现的经历之前就发生了,她预设了一个完美的自我形象,早早构筑起了精神洁癖。
与依利加雷异曲同工,克里斯蒂娃也试图超越拉康的阳具中心主义,将女性与“符号界”联系起来。在她的理论视域中,符号界与符号象征界对立,符号界的各要素(刻字、痕迹、指示等)包含了一切联系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驱力和母婴关系间的原初挂念2。女性联系于“前俄狄浦斯”的原发过程。这一阶段,父性大他者没有介入到主体塑造过程,分析的重点转移到了“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场域。继而将“母亲”角色提升到了关键位置。而将前俄狄浦斯阶段进行广义解读,柘榴对“前世”的想象移情就不难理解了。卓司接受“预定调和”,并立下7月20日为重返天空之日。柘榴却选择回到过去,回到现实还未被象征秩序染指的另一个生命当中。在那个世界自己还是处女,还能将自己的第一次交给喜爱的人。更重要的一点是,那个世界自己是包含了至善和污点的“完整的我”。对于柘榴而言,与其认为她在意“贞洁”这一父权象征秩序的符号而疯癫,不如说是“完整的我”大写物渗入象征界的欲望能指后带来的震惊。它告诉她:是时候颠覆了。
二、女性性欲和百合
克里斯蒂娃将女性与符号界联系起来,并认为符号界既包含想象界要素,也包含实在界的要素。那么这就牵扯到第二个话题,在拉康的论述中,想象界往往与镜像阶段的自恋幻想相联系,这也是分析爱情亲密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然而弗洛伊德、拉康等人对女性的探索亦被指责为一种“男性想象”。女性主义者亦以“窥镜”反过来透视男性对女性孜孜不倦探索的自恋本质3。女性欲望一直成谜。
有意思的地方在柘榴自杀之后的事情。如果将第三章与序章联系起来,“女性性欲联系于实在界”的结论呼之欲出。自杀之后,高岛柘榴的灵魂进入到了作为目击者的卓司无意识中,并最终发现自己爱上的卓司实际上是水上由岐人格(序章剧情)。即便如此,她对自己的真心毫无顾忌,并表达了自己对由岐克制的爱慕。这层欲望的关系则成了:要为卓司(由岐)献上第一次→不能接受被侵犯→追溯前世逃离现实→发现真相→笃定自己的欲望。到头来,柘榴接受了自己是一名同性恋者,和之前因为失去处女而陷入疯癫状态的柘榴判若两人。
正如依利加雷的观点,比起男性想象界中固着的女性印象和欲望投射,女性欲望存在更大的流动性甚至去性别化。这个理论的预设前提既是俄狄浦斯情结,我们不妨将“欲望”狭隘化为“性取向”以解释女性对百合的接受性。对于男女孩而言,他们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埃勒克特拉情结期)面临的状况是不同的。从拉康的镜子阶段我们了解到,前俄狄浦斯阶段,不论男孩与女孩他们的欲望对象都是自己的母亲。俄狄浦斯阶段初期,父性大他者闯入关系链,形式上构成了三人关系,主体的社会建构也开始了,男孩以为母亲的欲望指向父亲(实则指向他处),于是构建起了对父亲的敌视和对母亲的继续占有,假装自己拥有满足母亲的菲勒斯4(想象的菲勒斯)。俄狄浦斯阶段结束时,通过发现母亲的欲望永远指向无法捉摸的他处,并接受了自己并不拥有菲勒斯这一事实。男孩开始认同于象征的父亲,并认为从象征父亲身上能找到菲勒斯(象征的菲勒斯)。
女性埃勒克特拉情结期(荣格语)更为复杂,从开始到结束经历了两轮变换,女孩与男孩一样并不拥有菲勒斯,但是掩盖这种缺失的心理因素是不同的。男孩通过假装(pretend)拥有菲勒斯来“自以为是”地满足母亲,以解释恋母情节;女孩必须成为父亲的菲勒斯(因为父亲实际上也是被阉割的),以解释恋父情结。根据否定与承认的辩证关系,女性必须放弃自己“已是菲勒斯”,才能努力去“成为菲勒斯”。在如何“成为菲勒斯”这里,拉康又接受了里维尔的乔装(masquerade)概念,“女人味”如同“面具”一样可供穿戴5。在父权象征秩序下,女孩通过乔装隐藏起自己男性特质(满足母亲欲望的特质),以避免遭到男性的报复,但是这又让女孩陷入了和母亲的竞争当中。男孩与父亲竞争的解决方式是认同于父亲,远离了母亲。女孩也必须认同回母亲才能解除母亲的“敌意”,但是却无法逃脱“父名”的压迫和限制,这让女孩陷入了安抚父亲和安抚母亲的摇摆不定的两难困境。在阿比娜妮与弗雷斯特的眼中看来这种乔装与女性的本质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女性必须时而具备关于“拥有”的气质,欲望指向满足母亲(同性恋),时而具备关于“成为”气质,欲望指向成为母亲(异性恋)。因而女性和女性取向存在流动性,面具背后没有真正的“女人”。
总而言之,女性满足母亲欲望的原初动力,为女性的同性恋倾向埋下伏笔。当高岛柘榴通过自杀的方式,逃离了“自己被性侵”的那个世界而来到自己创造的新的世界中,由于菲勒斯的整体缺位,象征界的父亲法则不复存在,柘榴不再需要“乔装”成忠贞的女人,非常自然地接受了自己喜欢由岐的事实,从而解放了自己的欲望。当今许多百合作品也体现出这样一个特点,为了防止女性角色在性别气质比较中陷入被动,作品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彻底排斥男性的进入。提供一个女性舞台和女性叙事。当然,这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一旦将作品置于现实文化环境去理解,女性舞台又与观众呈现一个矛盾关系。当百合展现出来的,只是被资本认可的那一面时,它便无可避免地受到异化。
反思与拾遗
序章在整部作品中占据的位置有多么重要,仅仅从性别角度就能感受一二。它提供了一个克里斯蒂娃意义上的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母性空间”,杜绝了象征界的父亲介入。与第三章支线剧情一样,序章是一个没有菲勒斯介入的世界,理想的世界容器中只有女性之间的暧昧表达和盈溢的诗学。随着最后一名阳具持有者——音无彩名(扶她)被驱逐出序章,世界的完满性得以确立。而与第三章支线的不同之处在于,序章的呈现是彻底诗意化的,由于其美学高度拒绝了社会科学的简单还原,导致经验分析显得十分生硬。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尽管序章提供了一个美好的幻境,却也让笔者陷入新的迷思——如何解读柘榴所拥有的整个序章世界?提升到作品的创作来看,根本不存在能够被作者具体呈现出来的实在界。这种对实在界的具象化表达是存疑的。如果按照克里斯蒂娃的女性符号界的说法,序章毫无疑问是牵连“实在”。但是,我们该如何理解序章的“实在”性质?
序章通过美好的幻境,通过成人童话,召唤了与美好的百合情欲有悖的不协调。如果情欲如同无法解读的圣经文本中那个若隐若现的崇高的“质”,那么序章对女同性恋情欲的刻画,不过是形成了戏仿(parody)。它以一种有别于虚构的,“好像不是”的形式,让读者疏离于文本,以便让互文关系中的剩余召唤出来6。序章对《银河铁道之夜》的滑稽模仿可谓神来之笔,这则童话的暗喻似乎宣告着,序章无非是柘榴制造的又一场自恋幻觉,作为乔邦尼欲望对象的康贝内拉不可避免地离开他走向天国,乔邦尼最终意识到自己的欲望所指在不可言说的他处,进而长大成人。孩子最终脱离“母性空间”,走向恋父或恋母叙事。序章结局似乎是必然地,穿越幻想返回了象征界。剧情来到了黑暗又残忍的第一章,亦即那真实可怖的案件经过。
在此之中柘榴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拒绝原作者形象(音无彩名)的强加,以此达成对故事的反抗,构成了隐藏的meta成份。而这个成份为何不能以解构整部作品的面貌出现,或许又要追溯到整部作品的创作哲学——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世界是事实的全部。认识无法超越经验之外。
纵观素晴日,可以说高岛柘榴在剧中扮演了权力中心,至始至终控制着故事的走向,没有柘榴,整个故事几乎不能成立,序章恐怕也达不到一定的高度。其推动剧情的关键程度,以至于素晴日那些鬼畜的同人音乐基本围绕着柘榴的精神世界展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zakuro recording这张专辑)。这里笔者大胆猜想扶她自是否无意识发觉自己在创作剧本过程中若隐若现的菲勒斯中心,基于一种徒劳的否认,让笔下的柘榴憎恶自己的化身音无彩名。以达到自我阉割之意。这样,作为作者的扶她自就并不是通过给予和施舍,而是通过制造权力真空,让女性主体得以进入。在主流文化中,这常被用以批判“雄性衰落”,然而或许正是这种阉割,才打开了男性性别流动的大门。
至此,文章从简单的精神分析角度梳理了性别视角中的无意识主体和女性欲望的一部分。然而,虽然这一部分对于分析作品的性别意识非常重要,却并不意味着可以对这些粗浅的分析安之若素。本文有待回答的问题包括且不限于:
- 女性无意识主体的分析停留在了抽象思辨和规范上,并不能简单牵引到实然的、经验层面的分析。对于女性而言,还有更现实的、更广泛的问题值得讨论。而解决的关键是社会学意义上主体性,将无意识视为主体能动的一部分,以考察行动者的行动问题。
- 女性欲望的对象是什么?她不应该只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空洞能指,而且还应该是社会中某一具体指涉:如地位、权力、美的追求等等。性政治不可简单化约为无意识的分析。而是意识的,甚至是社会关系上的分析。
- “百合”并不与女同性恋直接等同,有时甚至完全背离真实情况,正因为百合涉及到更为深层的文化意义,使得分析“百合”变得状况复杂。百合必然被纳入文艺、文化视域与现实实践形成张力。
- “百合”的复杂性还体现在作品与社会文化的互构,男性欣赏百合的目的存在疑问。不可忽略百合作品中女性可能成为被凝视与消费的客体的情况,作品进而演变成“萌豚番”。百合作品的商品化包装多少消解了百合之意。
- 依利加雷的女性流动性的结论,仍然可视作一种本质主义(唯实论),在酷儿理论盛行的今天,是政治层面的倒退。尤其是忽略了女性个体间的差异,以及对跨性别者的冷漠。而性别社会学的分析不应拒绝多元。
- 同样,高岛柘榴的女性主义分析有将跨性别者隔离的风险。剧中柘榴拒绝了作为扶她的音无彩名的进入她的世界。将阳具隔离在了文本之外。从激进的性别自由论来讲,这看似是对阳具符号的“不公平”。
这些疑问或许可以通过对素晴日中其他角色的分析来解答一部分,下一篇,笔者将把目光放到现实行动层面,考察个体-社会,行动-结构,重点关注性别为何是展演性的以及性别实践问题。争取在文化意义上做一次广泛的诠释。这里同时要再次感谢大家的阅读。欢迎各位指正和提意见。
- 波拉·祖潘茨·艾塞莫维茨著, 金惠敏译. 露西·伊利格瑞:性差异的女性哲学[J].江西社会科学, 2004,3:202 ↩
- 不能按字面意思将俄狄浦斯、前俄狄浦斯理解成发展心理学中个体成长的两段时间。而要把它们视为影响并规定人类社会文化的“神话”,是“结构”而非“历史”的。但是,克里斯蒂娃借由“互文性”的概念明确表达概念的“发展变化”。详见:殷祯岑,祝克懿《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的发展流变》第63页。 ↩
- 伊利加雷在《他者女人的窥镜》指出,女性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视域下被认为是缺失的、不存在的。伊利加雷以“窥镜”的隐喻取代“镜子”意图放大并揭示精神分析的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概念的侵凌。见参考[1],202-203 ↩
- “菲勒斯”是希腊语Phallus的音译,指男性生殖器图腾,是精神分析中的关键能指(符号)。和解剖学的“阴茎”有重要区别。《导读拉康》译者李新雨将其翻译为“阳具”,吴琼《阅读你的症状》中写作“菲勒斯”,为尽可能避免误会,故取后者。 ↩
- Riviere, J.(1986[1929]) 'Womanliness as a Masquerade' , in V. Burgin, J. Donald and C. Kaplan(eds) Formations of Fantasy, London: Routledge, pp. 35-44 ↩
- 戏仿是对“神秘事物不可能的模仿”也是这种“不可能”的确认,有别于虚构。后者常常以否定神秘存在而制造孤立语境,以“肯定”虚构世界为形而上学终点。戏仿形成文本断裂能使读者疏离于文本,进而带来激进阅读的可能性。详见:阿甘本《渎神》78-8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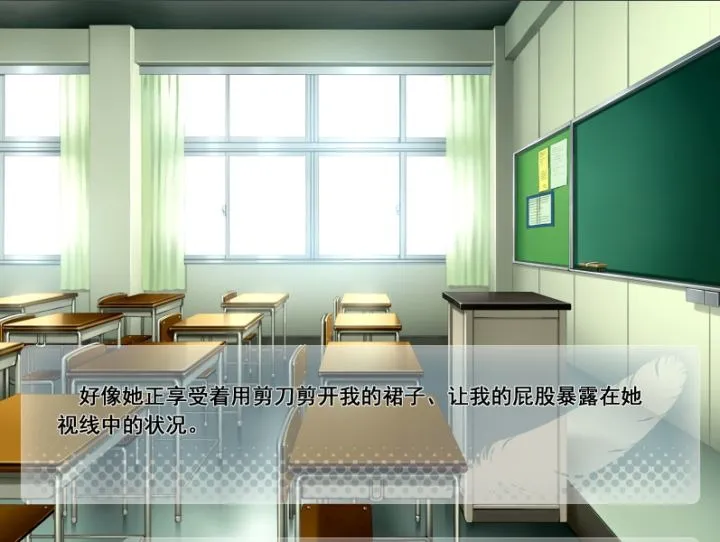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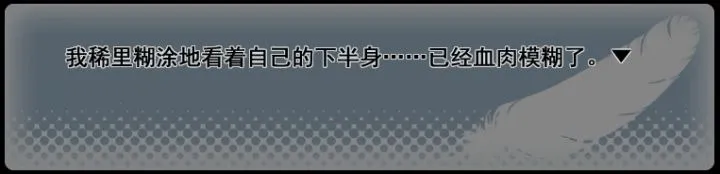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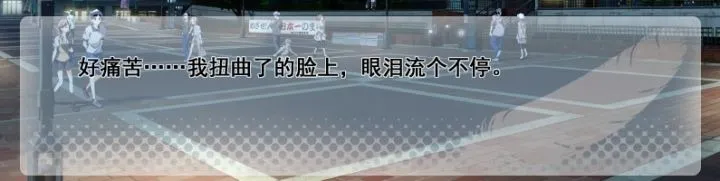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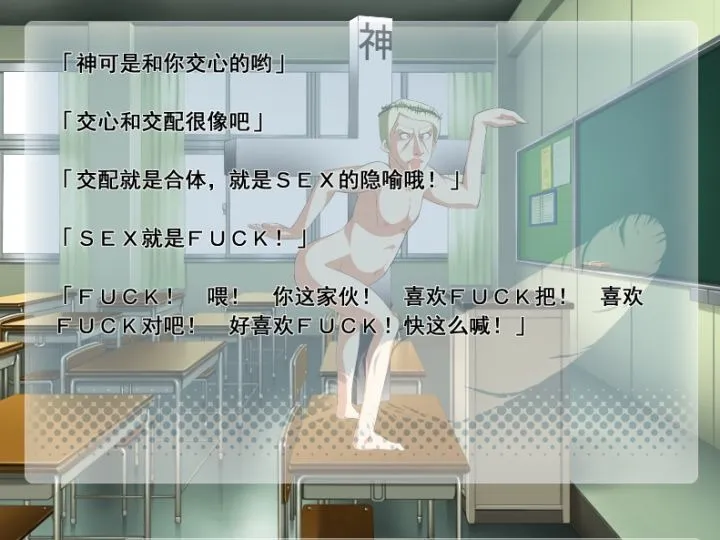











All gone(TNO既视感)